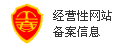早在1979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教授梅里曼等人在法律与发展研究(SLADE)中就以定量方式,从机构、工作人员、程序和消耗资源四个角度测算不同国家法律制度的实践运作状况。
要继续探索如何改进法院内部的审理分工,完善专利案件审理中民事、行政和刑事程序的衔接,逐步建立适合知识产权案件特点的审判机制。某省有个乡政府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被县法院撤销了几件后,该乡政府领导就扬言若法院再让他们败诉,换届选举时就不投法院院长的票了。

2006年底,肖扬院长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一份专项工作报告中指出,最高人民法院以学习和贯彻落实《监督法》为契机,主动接受人大的监督,并要求各级法院积极配合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在执法检查等具体监督活动中为人大常委会提供全面、准确的材料。[84]陈斯喜:《冲突与平衡:人大监督与司法独立》,《人民司法》2002年第6期。[6]参见前注[1],李飞主编书,第92页。在依法审理的同时,体现适当照顾的政策。对于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将及时制定整改方案,认真进行整改,并将整改情况向人大常委会汇报,听取人大常委会意见。
[17] 2007年,肖扬院长还特别提到,该院对《法官法》执法检查所提出的审议意见进行认真整改,取得了良好效果。截至其向常委会反馈情况时,所有案件都已落实到具体承办部门,4个案件已办结,其他都在审理、审查中。自治州人大常委会立法权的待区分样本包括变通规定和补充规定两类。
对于那些未涉及变通规定的自治法规,其与地方性法规的区别又何在?第二,并非所有变通规定均以单行条例为载体。至于实践立法需求如何回应,后文将有论述。那么,这些错位的单行条例在未来还能否再行修改?笔者同样倾向否定的立场。对民族自治地方而言,这种协调在城乡建设与管理、历史文化保护和环境保护三个方面均可呈现,亦能基于规范属性的一致而满足自治州-设区的市的协同需求。
[70]2001年的修法主要聚焦财政经济领域。[9]沈寿文:《民族区域自治立法权与一般地方立法权的关系——以优惠照顾理论范式为视角》,载《广西民族研究》2016年第3期。

这在学界一般被诟病为自治立法权的滥用——这类单行条例的性质,与一般地方性法规相似,但由于自治州和自治县没有地方性法规制定权,因此一些自治机关将其制定为单行条例。可见,赋予自治州一般地方立法权不仅是科学立法精神的充分体现,更是自治州内真正实现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的重要前提。若自治州选择行使自治立法权,则涉及上下级民族自治地方均履行自治权的情形。三是根据《立法法》76条的规定,本行政区域内重大事项的地方性法规只能由自治州人大制定,而关于X事项的立法究竟应选择一般地方立法权抑或是自治立法权,显然属于自治州的重大事项。
有观点认为《立法法》赋予自治州一般地方立法权的必然副作用,是挤占自治州自治立法权的空间。(图略) (图一) 二、一般事项抑或自治事项二选一标准的建构及证成 据图一逻辑,在情形②和情形中③中,一般地方立法权和自治立法权处于零和博弈状态,构成非此即彼的二选一关系模式,其关键即两类立法权各自固有、独占的立法范围的划定。[2]2016年3月24日,恩施州七届人大常委会对《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酉水河保护条例(草案)》进行了第一次审议。[37]沈寿文:《自治机关自治权与非自治权关系之解读》,载《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36]这些自治权在属性上仍然是自治权,只是在内容上与一般地方权力的界限不甚分明而已。由是反推,只要自治州需通过正式的立法来规制变通事项的,在形式上仅可通过行使自治法规制定权实现,这就排除了无变通功能的一般地方立法权被不当实施的可能性。

综上,自治州人大立法权的待区分样本包括自治法规、变通执行和停止执行三类。一方面,根据《立法法》75条第1款,自治州单行条例由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但省级人大常委会的拒绝立场却往往基于如下因素而不易形成:一是自治州立法本身属于其所在省级地方法治建设与发展成绩的重要组成。
理论上,解决的关键在于明晰民族自治地方两类立法权的楚河汉界,[5]但笔者认为这一思路在各项划界标准上均难以实现明确区分。[71]究竟以何者为主,应视具体问题以及该问题所处的历史背景和研究现状综合评判。简言之,针对同一立法事项,倘若将其移植到非民族自治地方,而该立法在结构、规范内容与规制目标甚至具体规则设定方面并无本质变化,则可基本判断其属于一般地方立法权事项,自治州在理论上自当通过地方性法规的方式实现法制化。倘若规制的视角和侧重并无明显差异,则仍以维护既有自治立法的法安性为主,确须修改的则依照法定程序修改。参见庞朴:《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载《东西文化与中国现代化讲演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页。第9条将档案建立、宣传教育、旅游娱乐等作为自治州的法定职责。
[15]这些单行法中的授权规定目前共有十几处,如《刑法》第90条、《民法通则》第151条、《婚姻法》第50条、《继承法》第35条、《妇女权益保障法》第60条、《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85条、《民事诉讼法》第16条、《收养法》第31条、《森林法》第48条、《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第68条等。民族既包括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也包括其他民族。
[6]学界一般将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统称为自治法规,参见沈宗灵主编:《法理学》(第3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68页。2.排除性依据:是否具有民族因素的判断标准 逻辑上,X属于纯碎的一般地方立法权事项的判断成立,除了其符合《立法法》72条第2款的范畴规则外,还应当反向排除其对民族因素的牵涉,原因是《立法法》所列举的可能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三类事项在逻辑上均存在与自治州当地民族因素相结合的空间。
在走出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的短暂低谷后,现行《宪法》第三章第六节不仅基本恢复了五四宪法的自治权条文结构,而且还进一步加以扩充,明确了人事权(第113、114条)、立法权(第116条)、财政权(第117条)、经济管理权(第118条)、科教文卫体权(第119条)、组织公安部队权(第120条)、语言文字权(第121条)以及获得国家帮助权(第122条)等8类自治权。[43]如承载着彝族撒尼人的经典传说——长诗《阿诗玛》(后被改编为同名电影),根据撒尼人民间音乐《圈圈舞》改编而成的经典歌曲《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等,均为附加于石林的重要文化元素。
判断的关键其实在于民族性因素与三类事项的契合模式。但由于是实质重合,故上级地方的一般性立法在本质上有悖于《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原则和宗旨,故自治州人大得通过行使自治立法权的方式出台相关规定,并根据《立法法》90条第1款之规定在事实上形成对上级地方既有一般地方立法的效力替代。可见,除体现为一般地方立法权的相关事项因被置于民族自治地方而晕染民族因素的情形外,前文论及的伪自治权问题亦属形式重合的典型代表。(一)情形②和情形③:单一类型立法权的错位及其纠偏 这种情形主要被描述为特定自治州针对X事项已制定有单行条例,而根据前述理论框架,X事项恰恰应当通过一般立法权实现法制化的情形。
[17]《立法法》原文表述为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这里的等应作等内等解释,具体论证参见郑毅:《对我国立法法修改后若干疑难问题的诠释与回应》,载《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1期。因此,下文将着重围绕前三种情形下自治州对两类立法权的选择问题分别展开论证。
此为自治县依法行使单行条例制定权的正当范畴,仍须回到大自治与小自治关系的理论框架中分析:若自治州选择行使一般地方立法权,则属于上级民族自治地方履行一般事权而下级民族自治地方履行自治权的情形。但作为替代方案,可能的法制路径有三。
由此,继五大自治区后,30个自治州亦形成了二元立法权格局:传统上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自治立法权,以及新获的制定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一般地方立法权。(一)情形②:仅属一般地方立法权范围事项的判断 1.直接规范依据:从《立法法》72条第2款展开 关于自治州地方性法规立法事项的范围,最直接的依据源于《立法法》72条第2款,即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和历史文化保护。
参见孙莹:《立法法修改对省会城市立法权的影响》,载《地方立法论坛·立法法的修改对地方立法的影响研讨会论文集》,2015年10月17日,南京。参见敖俊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释义》,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第36页。其一,在形式重合的情况下,自治州人大本来就具有选择具体立法权形式的自主空间。[30]可见,本民族内部事务理应包括各民族的内部事务(即民族事务),其中的各民族则以居住于特定地方为限。
一是在理论基础上,民族区域自治本身就是民族性与地域性的结合体,而地域性又恰是一般地方立法权被引入这一选择难题的核心路径。第一,在理论上,作为拉德布鲁赫公式的重要目标,法安定性一直是法律所追求的重要价值之一,其一方面体现为法规范的延续性,另一方面亦体现为对特定法规范解释的延续性。
若既有自治立法不符合实践发展,径依法定程序修改之。[33]此后,《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三章又将自治权规模细化至27项。
需要指出的是,并非官网所列举的一切职能均与城乡建设有关,如法制建设具有综合性特征,与其他分类并不适用统一分类标准,而风景名胜在修改后的《立法法》的语境中则应划归历史文化保护项下。[62]参见郑毅:《对新立法法地方立法权改革的冷思考》,载《行政论坛》2015年第4期。